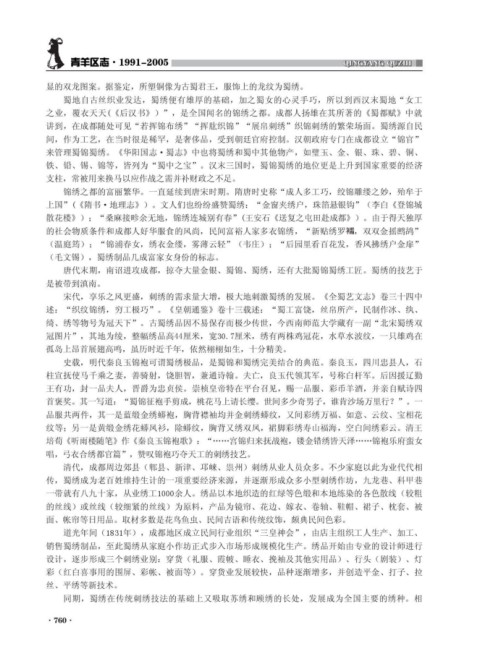Page 798 - 青羊区志1991-2005
P. 798
显的双龙图案。据鉴定,所塑铜像为古蜀君王,服饰上的龙纹为蜀绣。
蜀地自古丝织业发达,蜀绣便有雄厚的基础,加之蜀女的心灵手巧,所以到西汉末蜀地“女工
之业,覆衣天天(《后汉书》)”,是全国闻名的锦绣之都。成都人扬雄在其所著的《蜀都赋》中就
讲到,在成都随处可见“若挥锦布绣”“挥肱织锦”“展帛刺绣”织锦刺绣的繁荣场面。蜀绣源自民
间,作为工艺,在当时很是稀罕,是奢侈品,受到朝廷官府控制。汉朝政府专门在成都设立“锦官”
来管理蜀锦蜀绣。《华阳国志·蜀志》中也将蜀绣和蜀中其他物产,如璧玉、金、银、珠、碧、铜、
铁、铅、锡、锦等,皆列为“蜀中之宝”。汉末三国时,蜀锦蜀绣的地位更是上升到国家重要的经济
支柱,常被用来换马以应作战之需并补财政之不足。
锦绣之都的富丽繁华。一直延续到唐宋时期。隋唐时史称“成人多工巧,绞锦雕缕之妙,殆牟于
上国”(《隋书·地理志》)。文人们也纷纷盛赞蜀绣:“金窗夹绣户,珠箔悬银钩”(李白《登锦城
散花楼》);“桑麻接畛余无地,锦绣连城别有春”(王安石《送复之屯田赴成都》)。由于得天独厚
的社会物质条件和成都人好华服食的风尚,民间富裕人家多衣锦绣,“新贴绣罗 ,双双金摇鹧鸪”
(温庭筠);“锦浦春女,绣衣金缕,雾薄云轻”(韦庄);“后园里看百花发,香风拂绣户金扉”
(毛文锡),蜀绣制品几成富家女身份的标志。
唐代末期,南诏进攻成都,掠夺大量金银、蜀锦、蜀绣,还有大批蜀锦蜀绣工匠。蜀绣的技艺于
是被带到滇南。
宋代,享乐之风更盛,刺绣的需求量大增,极大地刺激蜀绣的发展。《全蜀艺文志》卷三十四中
述:“织纹锦绣,穷工极巧”。《皇朝通鉴》卷十三载述:“蜀工富饶,丝帛所产,民制作冰、纨、
绮、绣等物号为冠天下”。古蜀绣品因不易保存而极少传世,今西南师范大学藏有一副“北宋蜀绣双
冠图片”,其地为绫,整幅绣品高44厘米,宽30.7厘米,绣有两株鸡冠花,水草水波纹,一只雄鸡在
孤岛上昂首展翅高鸣,虽历时近千年,依然栩栩如生,十分精美。
史载,明代秦良玉锦袍可谓蜀绣极品,是蜀锦和蜀绣完美结合的典范。秦良玉,四川忠县人,石
柱宣抚使马千乘之妻,善骑射,饶胆智,兼通诗翰。夫亡,良玉代领其军,号称白杆军。后因援辽勤
王有功,封一品夫人,晋爵为忠贞侯。崇桢皇帝特在平台召见,赐一品服、彩币羊酒,并亲自赋诗四
首褒奖。其一写道:“蜀锦征袍手剪成,桃花马上请长缨。世间多少奇男子,谁肯沙场万里行?”。一
品服共两件,其一是蓝缎金绣蟒袍,胸背襟袖均并金刺绣蟒纹,又间彩绣万福、如意、云纹、宝相花
纹等;另一是黄缎金绣花蟒凤衫,除蟒纹,胸背又绣双凤,裙脚彩绣寿山福海,空白间绣彩云。清王
培荀《听雨楼随笔》作《秦良玉锦袍歌》:“……宫锦归来抚战袍,镂金错绣皆天泽……锦袍乐府蛮女
唱,弓衣合绣都官篇”,赞叹锦袍巧夺天工的刺绣技艺。
清代,成都周边郊县(郫县、新津、邛崃、祟州)刺绣从业人员众多。不少家庭以此为业代代相
传,蜀绣成为老百姓维持生计的一项重要经济来源,并逐渐形成众多小型刺绣作坊,九龙巷、科甲巷
一带就有八九十家,从业绣工1000余人。绣品以本地织造的红绿等色缎和本地练染的各色散线(较粗
的丝线)或丝线(较细紧的丝线)为原料,产品为镜帘、花边、嫁衣、卷轴、鞋帽、裙子、枕套、被
面、帐帘等日用品。取材多数是花鸟鱼虫、民间吉语和传统纹饰,颇典民间色彩。
道光年间(1831年),成都地区成立民间行业组织“三皇神会”,由店主组织工人生产、加工、
销售蜀绣制品,至此蜀绣从家庭小作坊正式步入市场形成规模化生产。绣品开始由专业的设计师进行
设计,逐步形成三个刺绣业别:穿货(礼服、霞帔、睡衣、挽袖及其他实用品)、行头(剧装)、灯
彩(红白喜事用的围屏、彩帐、被面等)。穿货业发展较快,品种逐渐增多,并创造平金、打子、拉
丝、平绣等新技术。
同期,蜀绣在传统刺绣技法的基础上又吸取苏绣和顾绣的长处,发展成为全国主要的绣种。相
·760·